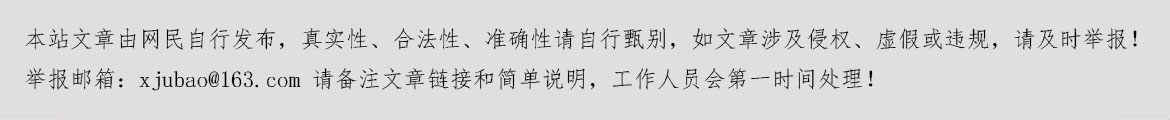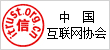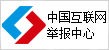八十年代的亚东老兵们,你们是否还记得一个小米玛的藏族姑娘?
2022-07-16 09:58:01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西藏亚东,凡是去过那里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叫小米玛藏族姑娘的记忆。或认识,或熟悉,或听说,或遇见……
亚东阿佳很妩媚贾洪国
有人说:“征服男人的,不是女人的美丽,而是她的女人味。”
什么是“女人味”?也许是她温柔的眼神,也许是她优雅的姿势,也许是她浅浅的微笑,也许是她真诚的问候,也许是她无声的关怀,也许是她妖艳的妩媚……风情万种是女人味,温柔贤淑也是女人味,母性的光辉还是女人味;温和开朗很有女人味,善解人意也很有女人味。能够发挥自己特点的女人同样都散发着女人味。
现在,社会上给女性赋予了一个几乎通用的称呼,那就是“美女”,甚至不分年龄,对年纪大的可以叫“美女奶奶”,对幼小的女孩子可以称她“小美女”,而对貌美如花的年轻女子称呼“美女”,那当然更是合情合理,对在职女性还可以称其“美女+职业”,如“美女老师”、“美女护士”……自然也明了而礼貌。实际上,“美女”的称呼,已经几乎与颜值无关。但是,你近乎可以认为我不入流,因为我几乎从来没有出声地称呼谁为“美女”过。
我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在我学生时代直至后来初踏入高原军营,没有敢称呼谁或陌生或熟悉的女子为“美女”,因为那时候称呼“美女”则有戏耍的味道。每一个女性都是指望你去尊重,去理解,而不是去赏玩的。同学间如果称叫她一声“美女”,后果可能是你会被骂惨,甚至可能会被她的家人或男朋友拳脚相加。只是,我虽然口上不曾叫谁为“美女”,但是心中自有美女,我想这才是我——正常的心理,当然,我心中的美女,离不开我对她经历环境的认可,更离不开我的偏爱。
回想一下,我在小学阶段,心中几乎是没有美女的,因为那时傻不啦叽的我甚至还分不清男女,我和男生在一起玩泥巴,却也和女生在一起跳皮筋,再说也有女生玩泥巴,更傻得可笑的是,有一次我几乎随着我的小姑姑(她只比我大一岁,在村小学上学),一起去上女厕所,还好,是她给我限定了入厕的方向。
参军来到西藏高原的时候,我开始心中有美女了,对驻地亚东的两三个藏族阿佳非常好感,用个时髦的词儿,或许她们就是我心中的“军花”,这个称谓不确切,因为当时六团没有女兵,440部队有三个,金贵得跟熊猫似的。我并且蠢蠢欲动地想在她们面前表现自己,而且甚至还英雄救美过,执行纠察时,我曾经为了她们训斥一名爱说俚语的老兵——这个老兵退伍后是某银行的行长——现在想来,我那时是真能义正词严!其中有一个阿佳叫“某某花”的,说话腼腆,未言即笑,体态如春红新绽,“闲静似娇花照水”,最能打动我的心,甚至让我不敢与她说话。一遇上她,我准脸红,准慌得语无伦次。这不,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觉得她很美,并且从来不敢去寻踪她,或许不忍看到她“人老珠黄”,或许是自私地怕破坏了她在我心中那美好的印象。
一个叫小米玛的下司马阿佳,喜欢和金珠玛米来往,谣传她的故事很多!“姿态优雅”,“婀娜多姿”,“边关雪莲”,“龙中一凤”……似乎这些词儿还不足以形容她,因为这些几乎都是赞美女生通用的词语。但是,我没有跟她说过话,再别说打过交道,只是有几回,在下司马巡逻纠察军容风纪,我随着六班几位战友,用目光把她从她所居住的下司马后街门口一直目送到邮电局女厕门外。当时况且不多了解她,自然现在想起还觉得有些滑稽。
终于在一个即将退伍离开亚东的黄昏,我特意借故去了一趟下司马,然后终于见到了她。她苗条的身材,成熟女性突出的曲线,白里透红的脸蛋,黝黑的睫毛衬托着一双明亮的眼眸,尤其是那一双明亮的眼眸……后来我退伍回到成都一家报社工作,听到歌星王菲唱《传奇》,“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的容颜……”依然还能想起这位美丽的藏族阿佳,当然,她则永远不会认识我。
其实,退伍离开亚东后,多少还有和那边战友书信来往,后来,也没有去问过比我后离开亚东的战友,小米玛和那个结的婚?仅为这个事由能去寻找昔日的藏族阿佳吗?有必要吗?
藏族阿佳,在奔波忙碌的农牧生活中,希冀有一臂膀可依,有一支曲子可寄,有一闺蜜可托,因为,藏族阿佳的心里,一直飘零着一片叶子。
亚东的藏族阿佳我只是觉得她们很美,自然跟我的恋爱生涯还似乎不能沾边。而我在《战旗报》学习结束回亚东的车上,也真的暗恋过一个叫普穷的藏族姑娘。她身材微胖,字写得很漂亮,特别是她一微笑,脸上必有两个小酒窝,温暖的会给人带来阳光、快乐的小酒窝。车到江孜住宿,出于军人学雷锋的必要,我帮她拧行李,帮她买吃的。我们相处得很好,且恰巧的是,她是一位县领导的千金,不敢摊事的我,回到亚东就一直不敢去见她,这段故事就此打住!
青春的荷尔蒙,促使思绪里老是凝望异性的倩影。小米玛就成了我们梦中的主角。记得86年的退伍季,小米玛是眼泪汪汪来到六团灯光球场为老兵送的行。头一天晚上,我站岗到子夜,看见她和一个退伍老兵在亚东宾馆亲亲我我,窃窃私语,我下岗了,他们还是依依不舍……
接下来,87,88两年的退伍季,我都在不同地点和不同时间,见到小米玛与退伍老兵,同样的依依惜别场景。不禁敬佩她的军民鱼水深情和藏汉一家亲的坚定践行意志!
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其实亚东人们的生活极其简单,包括她们的思想。我有次军民共建收割青稞,遇到过一些女子,也给她们拍过一些照片。她们的眼神一律清澈如水,因为从小信佛,她们的脸上便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虔诚。由于信仰的充实,我相信她们的精神生活也是充实的,但这些毕竟无法掩盖事实上的认知距离。
作为青春活力四射的年轮,我特别地留心路遇的那些女人。特殊环境的物质生活,令她们的身材走了样。缺乏成长中必需的营养,她们便有了肥硕的乳房;为了应付劳作而毫无节制地喂饱自己的胃,她们便有了鼓起的腹部。这在整天为减肥而节食奋斗的内地女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而她们就这样成熟于生命的轮回中,成熟于几乎没有什么外来人的干扰里,她们成熟于自然。她们就是这个高原上的一种产物,跟一块石头、一粒沙子、一朵不知名的小花一样,属于大自然。
她们是未经修饰的自然的生命,是坚韧而自足的生命。她们根本不会知道什么是名,也不知道什么是利。也许从夹缝里知道些世局,但并不关心。更可贵的是,她们大多都是快乐的。可她们又不刻意去追求快乐。这是最低也是最高的境界。
但不管怎样,亚东阿佳总是爱美的。从她们所穿的鲜艳的藏袍和佩戴的各种饰物中,无不透露出她们追求美的天性。
我在下司马一家小商店外再一次看到小米玛,她正对着橱窗玻璃当镜子照。她的指尖一下一下地抹过嘴唇,是在涂唇彩。她的指甲涂满鲜艳的寇丹。她的动作从容自然,就如她在树林里蹲下去一样自然。又好像那玻璃本来就是她家里的镜子。
我静静地看着,双眼忽然便有些潮湿。这位阿佳,以及生长在这里的阿佳们,她们多么像开在边关的杜鹃花!
女人,是多彩的风景,“女人味”确实无法作出简单的概括,但一个极有“女人味”的小米玛,总是在自然率真的洒脱中,流露出弥漫的温馨,流淌着浓浓的真情,展现着做人做事的艺术还有兼容并蓄的胸怀。那透着朴实无华的小米玛,她的处乱不惊的宁静心态和笑对兵哥的淡泊情怀,既平凡了亚东又深刻军旅。哪个兵哥不为之内心动容呢?
夏洛蒂·勃朗特在小说《简爱》里说过一段颇有经典意味的话
经常听说男人味女人味,你知道男人味是一种什么味道,女人味又是一种什么味道吗?男人味就是豁达勇敢,女人味就是温柔体贴。”
沉静的夜,习惯一个人静静的坐在电脑前,写点什么。此刻的我,思绪却有些凌乱,苦思冥想,也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面对着亚东那些文采飞扬、思维敏捷、知识丰厚、见解独到而备受读者喜爱的文章,看着自己这些浅薄、苍白、空洞的文字,感觉自己有些文思枯竭,有种“江郎才尽”之感,少了灵感的触动。
此刻的我不由自主地扭过头,扫了一下书柜里排列有序的书籍,似乎想从那里能找到一点点灵感。我站了起来,走到书柜前,仔细的翻看书的目录,期望它们能触动启迪我。瞬间,我看到了在书柜的一角,摆放着两本看上去似乎有些旧,书的纸张都有些微黄了,我知道那是我珍藏的《西藏日报》,《西藏青年报》的八十年代的合订本。这些合订本,搬了好几次家了,我都没有舍得丢弃,因为这是我喜欢的西藏军旅笔耕记忆。阿佳的美丽一直是我心中的偶像。我前后不知看过多少遍了,通讯的故事情节我几乎都能背下来。但还是百读不厌。
后来,我做了一个梦,梦中行走在坦荡开阔的拉(萨)亚(东)公路上,路两边花草树木丰茂,夏季,草木芳香盈盈,萦绕在鼻尖,融入呼吸,清洗腐朽堕落的沉积,心灵再一次醒来,迎接生的美丽。感谢天空和大地,只有在这里,我才可以放飞自我,像夏季小鸟儿一样,享受自由的风。
听一听鸟鸣,心就开朗了。它们才是军旅光阴里的故事,清脆亮丽的声音,没有什么音符可以代替,一切来自肺腑,成于天籁,静静地听,每一声都是“你好,爱你!”听一听鸟鸣,就走进了藏传佛教的天堂。听着听着,跟着小鸟的声声呼唤,所有的梦幻飞上了九霄。随风起舞的绿柳,在亚东的夏风里演绎生命的柔情,我和它对话,就找到了自由,柔情未必不成钢,记忆百炼写沧浪,摇尽军人心间事,只把秋风化谷黄。
(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贾洪国:1968年生人,西藏军旅五年,双流县报记者十年。出版有个人文学集《一花一世界》、《人生足迹》、《风兮雨兮》。近年来,主要精力用于采写《寻访战友故事集》,目前已完成了二十多万字的初稿创作。因为“人在变老,军旅的记忆却永葆青春!”把文字当成爱好经营,把生活当成诗意品味,一念花开,一念云起,在时光中拈花微笑,能穿透岁月的漫漫尘埃。
贾洪国
http://www.chushuping.com/chubanzhishi/